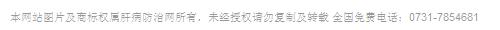作者:卢继全,医院野战医疗所第一医疗组军医
美篇制作:老哥
我年参军,那年我十六岁,然后长期工作在解放军第医院,主攻耳鼻喉科,医院退休,但又作为专家返聘继续工作在医院,在长达47年的岁月里,我一直工作生活在人民军队中。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已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为满头白发的老人,记忆远不如当年,但内心深处始终清晰地印刻着年那段战火硝烟的经历……。
一、出征名单的揭晓
年10月,我所在的医院按上级命令进入战备状态,年底频频传闻中国政府要对越南的边境挑衅行为进行自卫还击。到了年1月,消息就更加明确,说我们医院要成立实战性的野战医疗所开赴前线,编制80人,具体名单却迟迟没有公布,这引来各式各样的猜测,大家的情绪都比较紧张。
我是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我们科只有两名医生,另一名医生的妻子刚怀孕6、7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我判断应该是我出征。我年12月底结婚,妻子是医院一外科的护士龙丹玲。按照规定,医院都设有战备性的野战医疗所,要经常进行备战训练,我妻子几年前就是野战医疗所的骨干成员,这次出征估计也少不了她。我们夫妻都认定自己会出征,内心反而不感到焦虑,非常平静地等待出征名单的公布。
2月15日下午5点,医院突然通知我,马上准备,晚上8点准时出发,奔赴前线,这也意味着出征名单终于揭晓了,名单上没有我妻子。
我和妻子一起赶回宿舍收拾行装,背上背包,医院大礼堂门前集合,发现出征的人员还有:医院副院长马德良、政治处副主任张如日、院务处副处长方忠广、五官科主任邱锦信、五官科敎导员谭亦运、外科主治医生陈志坤、孔禄生,我军校的同学万新祥、邓贵江等,令我惊讶的是,我军校同学范垂利的妻子刘建辉产后才3个多月,也要随队出征,后来听说有个标准,双军人夫妻必须去一个人,因为她丈夫刚好在外出差,一时赶不回来,所以只有她去了。
登车前,医院党委和留守人员都来送行,出征人员纷纷向院党委递交请战决心书,现场气氛既热烈又凝重。
二、第一天的忙碌救护
2月17日早上6点05分左右,天还未亮,我们抵达上石军需仓库,仓库建筑面积很大,火车可以直接驶进仓库卸载物资,这是我们野战医疗所的第一个驻扎点。
背包刚放下来,野战医疗所领导紧急集合队伍,宣布中央军委命令:为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军委决定从2月17日早上打响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话音刚落,中越边境地区就万炮齐鸣,半边天都被炮火烧亮了,耳边不停地回响着“轰轰轰”的炮声。野战医疗所马上进行任务分工,医疗展开。
我们野战医疗所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前接后送,前面下来的伤员,经过我所检查急救处理,再转上火车,医院进一步治疗,保证伤员在转送过程中能得到医疗保障,避免伤势恶化。
我们野战医疗所分为两个医疗组,我属于第一医疗组,组长是孔禄生,医生有我和邓贵江、吴朝阳、黎炳尧,护士长是张凤春,护士有黄小冰、安秀云、丁湘陵、贺红枫、陈和平、李曼玲、李生粤、朱坚东,卫生员有梁秀媛、杨洁球、叶运浓、何翠英。
在等待伤员期间,我们医护人员抓紧时间写下了遗嘱,因为毕竟是在战场,谁也不能保证不出意外。
从下午4点30分左右,突然从前线下来80多台装满伤员的解放牌汽车,车队绵延达一公里,陆续驶进上石军需仓库门前的平台和相邻的坡地,紧张的救护工作开始了。
由于伤员比较多,有的一台车都有10多名伤员,野战医疗所怕伤员随便下车造成混乱,便要求伤员一律不得下车,由野战医疗所医护人员在车上作检查。
第一医疗组安排我带上一名护士黄小冰登车检查,筛选急重伤员。我戴上听诊器,在黄小冰护士的配合下,一辆一辆车地检查,有些伤员躺在车厢内,我在检查时往往要蹲着,最后干脆跪在伤员旁边,先询问、再摸脉、然后检查伤口。
在交谈中,我了解到伤员们从受伤到转运至这里,已有八九个小时没吃没喝,加上紧张焦虑,所以心情非常不好,不停地抱怨指责,个别伤员还爆粗口骂人,我和护士黄小冰边检查边安抚伤员情绪,还总结出了一个规律,不停抱怨、声音嗓门大的伤员,一般没啥大问题,越是不出声的,越要重点
转载请注明:http://www.tdghe.com/wgkjbyf/832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