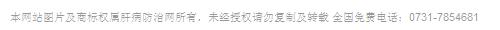作者简介:
陈柏萍,青海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史研究。
张科,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史研究。
(本文发表于青藏高原论坛,年7月第3期,原文版权归原刊物所有。)
摘要清民国时期青海蒙古族受居住环境、政治生态环境、宗教信仰、蒙藏间的通婚等因素的影响,其语言文化涵化现象特别突出。经过三百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清民国时期青海蒙古族语言文化涵化呈现出蒙藏杂糅,蒙中有藏、藏中有蒙,以及由于聚居区域的不同,青海蒙古的语言文化多元化发展态势。
关键词清代;民国时期;青海蒙古族;语言文化;涵化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标志,语言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承继性,但非固定不定,它随着该族群活动空间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青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之地,又是农牧经济并存的区域,东部湟水河流域是农耕经济,日月山以西区域是游牧经济,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交融互补;同时多民族聚居形成了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信仰的共生和相互影响。清代和硕特蒙古部移居青海后,在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浓郁的藏文化包围下,特别是经历罗卜藏丹津事件后,青海蒙古族从政治上的优势族群,沦落为受清中央打压的弱势群体,在清朝推行的旗制下,其民族内聚力涣散,遂导致其语言文化教育相应地出现藏化或汉化的趋势。目前学术界对清代及民国时期青海蒙古族语言文化涵化现象鲜有涉及,本文拟就这一现象作一探析。
一、从蒙古语为主转变为藏、蒙、汉三语兼有++清代,居住在蒙古高原和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蒙古族普遍使用的是成吉思汗时期所创制的蒙古文字(亦称胡都木蒙古文);居住在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境内的蒙古族使用的是托忒蒙古文。托忒蒙古文是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①制的。他根据卫拉特地区的发音特点,在顺治五年(年),将回鹘体蒙古文改革成“托忒文”。“托忒”是“明了、清楚”之意。托忒蒙古文与胡杜木蒙古文相比,具有下述三个特点:一是创制了标记长音的符号“┠”;二是采用特殊符号区别其37个短元音;三是由于使用了字母圈点等附加符号,使每个字母基本上做到了一字一音。托忒蒙古文由于与卫拉特口语接近,所以,很快在卫拉特蒙古诸部中得到推广和使用。整体而言,卫拉特方言具有与元音的阴阳性相关辅音和谐的古代蒙古语痕迹。[1]
和硕特蒙古从新疆移牧青海后,非常重视对贵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在《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中明确规定:“诺彦贵族十岁以上的孩子必须读书识字,违反者罚马一匹,较富裕家孩子没有读书,罚牛一头,平民孩子未读书的,向佛祖磕一百个头”。[2]到康熙朝中期,托忒蒙古文字已经在青海蒙古贵族中得以推广和应用,其与清朝间往来的公文、信函都是用托忒蒙古文行文的,尤其是寺院的经济账目和档案、历史、文学著作也都以托忒蒙古文记述。对此,清中央理藩院设有托忒文馆。雍正年间,青海蒙古被清朝直接统辖后,清朝明确规定,青海蒙古各旗王公台吉向朝廷或西宁办事大臣衙门的奏折必须用蒙古文。[3]清末,清朝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新政。为了贯彻清中央旨意,宣统二年(年),西宁办事大臣庆恕奏请从丹噶尔厅盐税拨银八百两,创办蒙古半日学堂。学堂地址在西宁南大街印心禅林(又称印心寺)。蒙古半日学堂专门招收青海蒙古族的王公子弟,招收名额按旗分配。学堂创办之初,只有一名教师,十几个学生,学堂主要用汉语给学生讲授《三字经》。学校每月给每个学生伙食费一二两。[4]进入学堂的蒙古子弟开始从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转而使用汉语言文字。所以说,青海蒙古诸旗对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不仅日趋萎缩,而且逐渐呈现出被藏语或汉语所替代的趋势。黄河北二十四旗蒙古中,除了和硕特西右中旗、北左旗、北右末旗三旗比较重视蒙语而能保守蒙古固有文化者外,[5]其余诸旗蒙古族通晓蒙、藏两种语言。19世纪前,聚居在祁连、青海湖南岸和东北岸的蒙古人基本上还能用母语进行交流,可是,上层王爷与僧人交谈时已开始使用藏语。[6]然而到了清末,居住在这一带的蒙古人有些只懂藏语,而不会蒙语。俄国探险家崔比科夫途径茶卡地区,对所见到的蒙古人描述道:“像所有普通青海蒙古人一样,受到唐古特人的强烈影响……,从外貌上看纯粹是个唐古特人,也讲唐古特语,进一步交谈后才发现他是蒙古人,但他的母语很差,以至于不能交谈。”同至民国时期,随着大量的汉族、回族进入青海蒙藏地区经商或农耕,久而久之,汉语也在蒙古民众中流行开来。青海湖南同德县、共和县和青海湖北海晏县、祁连县、门源县及黄河南境内的各旗蒙古,已经尽弃蒙文而用藏文,除老人外,三四十岁下的人,大部分都不舍说蒙古语。[8]民国末,杂居在汉、回之地的青海蒙古“能通蒙文者,竟十不得一”。[9]聚居在黄河以南的蒙古诸旗则已经通用藏语和藏文,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老人懂得蒙古语言文字。散居在东部农业区的蒙古族不仅全都通用汉语言文字,甚至连民族身份都发生了变化,有些成为土族,有些成为汉族。
二、清代及民国时期青海蒙古族语言文化涵化的原因分析(一)政治生态环境变化是造成其语言文化涵化的根本动因早在清朝还没有入关之前,和硕特蒙古就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占领了青海,进而控制了康区和卫藏,结束了青藏高原自元以后四分五裂的局面,建立起了和硕特汗廷为中心的统治机构。汗廷的中心虽然在拉萨,但后方基地是青海,固始汗将其部众从新疆移牧青海地区后,为了强化对青海的统治,把自己的八个儿子封为领有世袭领地的领主,让他们及其后裔率领属部驻牧在青海湖及其周边地区。为了便于对各级封建领主的管理,从中选一子为珲台吉为(总管王),又将青海蒙古分成为左、右两翼。这样,就形成了和硕特汗廷大汗之下,以珲台吉为首,有左、右两翼翼长、八大台吉共同参与理政的行政系统。以珲台吉为首的青海蒙古王公贵族通过祭海会盟的形式来商讨军国大事。这一行政体制看似松散.但它有一个以珲台吉为首的核心首脑,而且还有地位不等的各级领主,上下之间界限明确,具有很强的行政隶属关系。加之青海蒙古很早就与满清政权建立了关系,满清政权定鼎中原后,因忙于政权内部的稳定和中原地区的经营,对青藏地区采取羁縻统治的策略,承认了青海蒙古贵族对这一地区已有的统治,所以,在长达近八十年的时间内,青海蒙古在青藏地区居于统治民族的地位,政治生态环境的优越性和所控区域面积辽阔,使自身的语言文化发展空间较大。但随着清廷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强化,特别是清朝把西藏直接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下,并把由青海蒙古控制的康区分别划归到四川、云南后,青海蒙古的活动空间不断缩小,统治地位也开始下滑,特别是经过罗卜藏丹津事件之后,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争斗中,青海蒙古封建主一败涂地,其原有的行政体制被彻底取缔,清中央把青海蒙古划分为五部二十九旗,互不依附,且各自为政,“每札萨克俱设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员;每佐领俱设佐领、骁骑校,催领四名;其一旗有十佐领以上者,添设副协领一员,佐领二员,酌添参领一员”。[10]还为每旗划定地界,不准越界放牧,不得私自往来,并设置卡伦。这种行政分割带来的后果是:原来归和硕特蒙吉族领导的统一的青海蒙古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受西宁办事大臣管辖的青海蒙古地方政权。原来的部族被分化为二十九个旗,各旗设互不统属的札萨克等,所属旗实际上成为了他们的封地,因而原来部落人与人之间的血缘意识淡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或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生活上的联合体开始解体,彼此间不仅在实际利益上,而且在心理意识上出现隔阂和对立,最终导致青海蒙古自身语言文化使用范围不仅受限,而且发生涵化。
(二)居住环境的影响清代早期青海蒙古族在政治上虽然居于优势,但从人口数量上而言,依然超不过藏族。所以,蒙古族移牧青海后,就处于四周被藏族部落包围的环境中。雍正以前,在清朝中央的支持下,青海蒙古在政治地位上占据绝对优势,而青海藏族自明朝中叶始,一直受青海蒙古的役使,所以藏文化对青海蒙古的影响还没有突显出来。但并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其蒙古方言中大量吸收了藏族的生活用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卫拉特青海方言就是一个明证。而且,部分青海蒙古王公贵族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在继承、保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不仅接受藏文化,还积极倡导和学习藏文。以河南亲王为例,达尔加·博硕克图济农于顺治九年(年)从青海湖北部的皇城滩南迁至黄河南部后,其周边均是藏族部落,为更好地在此地进行统治,与周边藏族部落建立友好的关系,不仅聘请蒙古学者给自己的子弟讲授蒙文,还聘请藏族学者给自己的子弟教授藏文。而且河南亲王府将这一做法沿袭下来,到丹增旺舒克袭河南亲王位后,进一步加大了教授藏文的规模和内容。据说,丹增旺舒克从西藏聘请了一百多位高僧到王府,除部分留在王府担任文职事务外,其余的给王公子弟教习藏文、佛学、医药学、天文、历法、音律等方面的知识。[11]河南亲王府内设有蒙、藏文秘书。与此同时,为青海蒙古族培养了一批精通蒙、藏两种语言的人才和学者,如察罕丹津之子敦多布旺札勒(藏文名字端智昂加)精通蒙藏两种文字,郡王纳罕多尔济(又译为俄巷达杰)不但通晓汉、蒙、藏三种语言,还精通语言学、医药学,有很深的文学造诣。[12]嘉庆、道光时担任王府秘书的阿尕才让用蒙文撰写的《先祖传记珍珠璎珞》,该书对和硕特部历史进行了记述:道光二十八年(年),王府秘书昂青嘉布在《先祖传记珍珠璎珞》的基础上,用藏文编纂了一部记述河南蒙古族历史的《先祖言教》一书。所以,在河南亲王的大力倡导和率先垂范之下,黄河南的蒙古族逐渐放弃了对本民族文字的学习和传承,转而学习藏文。[13]至民国末年,黄河南四旗中陈前首旗外斯部落、南中旗达参部落的部分牧民会说蒙古语外,[14]其他诸旗除老人外,三四十岁以下的蒙古人,绝大多数都不会说蒙古语。[15]就连当时的亲王扎西才让自己既不识蒙文,也不会讲蒙语,却谙藏文。[16]原来亲王府内的蒙古文秘书已不见踪影,只有藏文和汉文秘书。
雍正年间以后,清廷推行蒙藏分治和“扶番抑蒙”的政策,青海蒙古人受到重创,政治地位的丧失,经济权益受损。摆脱了青海蒙古统治的藏族各部人畜繁殖很快,青海蒙古诸旗人畜减少,势力日衰,不仅难以守住自己的驻牧之区,还无法抵御周边藏族部落的劫掠和蚕食。嘉庆、道光年间藏族部落渡河北移和环海藏族部落的形成,一方面打破了清廷南番北蒙、蒙藏分离的分布格局,形成了蒙藏的杂处共居:另一方面,加速了蒙藏两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使处于弱势的青海蒙古族语言文化呈现出藏化发展之趋势。只有居住在柴达木盆地(今海西自治州德令哈市、乌兰及都兰地区)的和硕特部西后旗、西前旗、北左旗、北左末旗、北右末旗、西左后旗、西右后旗、西右中旗等八旗之蒙古人,由于聚居区相对封闭,所以,才能够将蒙古语言文化传承和保留下来。
柴达木(蒙古语,盐泽之意)盆地属高原封闭性内陆盆地,东西长约千米,南北最宽处约千米,面积为25.66万平方千米,占今天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面积的85.28%。盆地四周环绕着昆仑山脉、祁连山脉和阿尔金山脉,平均海拔米以上。盆地从边缘到中心依次划分为高山、戈壁、丘陵、平原、湖沼5个环形地貌带。盆地内温度较高,分布着许多的咸水湖和盐湖及沼泽地。气候干旱,降雨较少,植被覆盖率低,乔木类植物有杨、柳、祁连圆柏、青海云杉、胡杨;灌木类植物有沙棘、沙柳、唐古特白刺、梭梭、骆驼刺等等。恶劣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居住在此的蒙古诸旗间联系密切,却与盆地之外的蒙古人隔离,才能够使其将母语保留传承至今。民国学者马鹤天在《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写道:“柴达木诸蒙旗,因其地为沮洳,土多碱性,春夏满泥,夏秋多蚊,他族不适环境,蒙民遂得生存,迄今尚保存其纯粹蒙古生活”。[17]
(三)宗教信仰的因素藏传佛教是青海蒙古族语言文化逐渐藏化的融合剂与助推器。青海蒙古人自明代万历年间开始就已经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和硕特蒙古在移入青海之前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忠实信仰者,它又是打着援助格鲁派的旗帜进入青藏高原,进而立足于此地。为了表示自己对宗教的虔诚信仰,青海蒙古王公贵族聘请高僧担任王府或札萨克府邸的经师。这些高僧不仅承担着为王公贵族念经祈福的职责,还给王公贵族及其子弟教授藏语言文字和佛学经典。与此同时,青海蒙古贵族不仅给自己辖区内格鲁派寺院划拨大量的土地和财物及百姓,如固始汗于年将湟水河以北的华热地区献给郭隆寺法台南杰班觉,作为郭隆寺寺属庄园;将湟源日月山和今海南州共和县倒淌河一带的大片土地赠给东科尔寺作为属地。还广建寺院,选送子弟入寺学习,如康熙四十八年(年)建拉卜愣寺时,河南亲王察罕丹津向寺院输送三百名蒙古族青少年作为僧源;乾隆二十年(年),亲王丹增旺舒克亲自赴卫藏地区,迎请甘丹寺第五十三任池巴萨木察·坚参桑格回籍弘扬佛法,修建郎木寺作为其驻锡之地,并从黄河南蒙古诸旗中选派五十名青少年作为该寺僧源。[18]鼓励蒙古族王公子弟和青少年出家为僧。如达加尔·博硕克图济农的长子岱青巴图尔(又名才项华贲、埃克岱青)曾入札什伦布寺为僧,其子车臣固达赖喀木布为塔尔寺的堪布;河南亲王更噶环觉曾入拉卜愣寺为僧,南右中旗札萨克沙拉布提理曾是隆务寺僧人。[19]由于僧人在当时蒙藏社会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加之早期在青海蒙古只有王公贵族和家庭富裕者才能请得起老师为孩子教授文化,普通蒙古子弟要想习得知识,只有进入寺院。所以,寺院不仅是蒙古族民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还承担着向蒙古族子弟传授知识的功能,青海普通的蒙古族家庭除留一个或二个孩子协助父母放牧外,其余的孩子都会送到寺院为僧,在寺院接受教育。清朝晚期,青海蒙古民众生活陷于贫困的境地后,许多蒙古人为了活命,也纷纷出家为僧。
有学者统计,截止年,“全省以蒙古族为主要僧源的藏传佛教寺院约十八座,均建于清代或民国时期,除一座是格鲁派和宁玛派合住寺院,其他均属格鲁派。其中海西十寺,海北二寺,湟源、海南各一寺,河南县四寺。”[20]但据笔者查阅,青海蒙古族修建的寺院很有可能不只十八座,这里面还不包括一些简陋的帐房寺,详见下表。
清民国时期由青海蒙古王公贵族出资在青海地区修建或以蒙古族为主要僧源的寺院
资料来源:卓仓·才让:《黄河南蒙古志》;蒲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年治海,白更登:《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明鉴》整理而成。
上述寺院中,以扎藏寺和都兰寺知名度最高。因为扎藏寺不仅是青海蒙古格鲁派的主寺,也是早期青海蒙古王公贵族协商政务之地,青海蒙古王公在此建有府邸(俗称衙门);康熙年间,清朝在这里设立行官,作为与青海蒙古王公进行沟通及会盟的处所。都兰寺是蒙古族在海西地区建立最早和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是清代中期青海右翼蒙古政务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和互市之所。但由于这些寺院内都是用藏语言文字来讲授佛教经典和文化的,在寺院为僧的大量蒙古族不仅率先接受了藏族语言文字,而且还成为藏语言文化的传播者;许多蒙古族群众为诵经的方便,也选择了藏语。罗卜藏丹津事件后,青海蒙古贵族政治地位下降,转而把精力投入到虔诚的宗教信奉上,因为大部分佛教的典籍都是用藏文撰写和用藏语诵读的,所以,为诵读佛经之需,许多蒙古王公贵族及民众开始习用藏语,蒙古的学者们直接用藏文来撰写自己的历史、文学;即便是日常的“书函往来,蒙人亦以藏文书写,都把自有的蒙文抛在一面,少应用它,因为这样蒙古人虽然仍然讲着自己的蒙语,但因为普通使用藏文的缘故,蒙古语言内也混杂了许多藏语在内,真的与内蒙的语言有了许多不同的事实。……至于尚能保持自有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的其他蒙旗,也因佛教教义的陶融,都在被受西藏文化的激荡,改变自有文化的可能中。”[21]寺院教育成为青海蒙古族教育的主体后,虽然为青海蒙古族培养了许多精通佛教理论的高僧大德和许多精通藏语言文学和掌握天文、历法、医药学等知识的专业人才,如年,青海蒙古人占布拉用藏文撰写的《满阿嘎仁钦纵乃》(藏名,汉译为《方海》),该书记载和收集了外、内、儿、妇、五官科和传染病、热病等各科临床医疗的药方种,涉及余种药物,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蒙药选集。但也造成传统蒙古族语言文化传承场所和使用范围的萎缩。因为寺院里用藏文来传承宗教知识、天文、历法、医学等。所以,其语言文字深深打上藏文化的烙印,表现为在日常的书信往来中的藏文多于蒙古文,即使用蒙文进行交流,其中也掺杂了许多藏语的词汇,有些蒙旗甚至直接使用藏语,就连蒙古人比较多的海北之海晏,“蒙古语亦有隔阂之处”。通译多以藏族为主,要求其蒙古语“稍通其意”即可,与蒙古人交往时,说蒙语,若有不懂之处,说藏语则“无不解”。民国年间,除公文兼用蒙、汉文外,余多用藏文。[22]
(四)蒙藏间的通婚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单位,婚姻是一个族群人口繁衍发展的重要依托。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一个民族的强盛和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人口的多寡来实现。蒙古族历来将家庭婚姻看成是维系民族和保持本民族血统纯正的主要渠道。清初,青海蒙古族各级王公贵族和少数富人存在一夫多妻,广大牧民仍以一夫一妻为主。婚姻盛行民族内婚制,为了避免近亲结婚,规定同宗不婚,同一部族内也禁止通婚。等级婚明显,王公贵族之女绝对不允许下嫁给平民之子,一般贵族富户可以娶平民。为保证骨系和血统的纯正及家庭财产的完整,流行收继婚制(亦称转房婚制),即“兄终弟纳嫂,父死娶庶母,子死翁收媳”。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廷为了彰显自己对青海蒙古所拥有的绝对权威,按照儒家的人伦观点,明确规定“父没不许娶继母,及强娶兄弟之妇”。[23]从而根除了在蒙古民族中实行了数百年的收继婚旧俗,把青海蒙古民族的婚姻纳入到儒家文化的人伦规范内。蒙古族进入青海地区后,数量远不及藏族,出于巩固蒙藏上层联合统治的需要,蒙藏两族上层之间很早就开始联姻,如清代青海蒙古贵族多与西藏上层僧侣家族联姻。雍正年间编旗划界后,青海蒙古各部被严格限定在固定的区域内,以避免近亲结婚,到19世纪后期,青海蒙古族开始与周边其他民族相互通婚。其中以蒙藏间通婚居多,不仅有普通的百姓,而且也有蒙古上层王公贵族。当然,蒙藏上层间的联姻虽有繁衍子嗣的需求,但更多的出于双方各自的政治利益的考虑。较为典型的是黄河南亲王与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家族累世有姻亲关系,第四代亲王纳罕达尔济娶二世嘉木样之妹仁增项毛为妻;第五代亲王达什仲鼐娶二世嘉木样侄女为妻;第八代亲王巴勒珠尔喇布坦娶四世嘉木样胞姐之女滇吉环仲为妻,第十代亲王札喜才让则招五世嘉木样的侄子黄文源为驸马。早期双方联姻出于以政扶教,后期则是以教固政,使双方在黄河南地区的政教统治互惠互利。民国初年,默勒王旗札萨克棍布拉布坦娶阿柔部落千户南木卡才巷的妹妹尕昂。棍布拉布坦去世后,南木卡才巷不仅将其妹妹和外甥宫保多杰接回本部落抚养,且待官保多杰成年后,还亲自奏请蒙藏委员会批准其袭札萨克一等台吉之职,并出资帮官保多杰娶了贡王爷的三女儿。[24]这种联姻不仅密切了双方之间原有的亲情,也使南木卡才巷博得了好的名声,并为自己的部众找到了新的驻牧之地,因为贡王爷晚年时将默勒王所属地盘及契约交给了南木卡才巷,阿柔千户才得以率领所部离开黄河南来到今海北一带,并借助驮勒札萨之名管理该地区蒙、藏两族一切政教事务。[25]由于蒙藏两族生产、生活方式相同,宗教信仰也相同,所以,普通平民之间的通婚更为普遍,至今阿柔人“普遍认为自己的母系是蒙古人,父系是阿柔人。”[26]除藏族外,一些经常到蒙、藏地区去经商的汉、回商人或歇家的店主,也有与蒙古人“私相结婚者”[27]。据《丹噶尔行志》载:“尝见蒙古男子供差公门,衣冠楚楚,其妻室则番装也。其子娶汉女为妇,再生子女,皆汉族也,此变俗之渐也。”[28]青海蒙古与其他族群之间的通婚,也加速了蒙古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进程。
三、清代及民国时期青海蒙古族语言文化涵化的基本特征明末,蒙古族移居青藏高原后,脱离了蒙古语母语生成的大环境,在青藏高原浓郁的藏文化氛围中,蒙古族、藏族长期交错杂居,共同的游牧生活及共同的宗教信仰,特别是经历罗卜藏丹津事件后,青海蒙古人口一直处于减少的状态,从前期的蒙强藏弱变为藏强蒙弱,这种政治优势地位的逆转,逐渐导致青海蒙古自身语言文化弱化,并开始向藏化、汉化转变。整体而言,清代青海蒙古族社会文化受藏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族群蒙藏杂糅,蒙中有藏,藏中有蒙,互相融合。蒙元时期进入青海的一部分蒙古部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当地藏族或其他民族所融合。如,在今青海的果洛地区,仍有一部分人自称其祖先来自于蒙古皇室或蒙古部。[29]四川西北的霍尔五部“均非土著民族,殆来自青海”。[30]甘孜州邓柯村的村民自称是明末活动在青海地区的火落赤之后裔;固始汗第五子伊都勒其之子罕都占领康区后,由于势力过大,招致其亲族兄弟嫉妒被杀,其部众也逐渐融入到当地藏族中,今青海玉树州囊谦县境内的大小“苏芒”、“蒙古尔津”、“白力登马”、“竹节族”等均属罕都部众;[31]居住在今天西藏当雄的达木人,从根子上讲,是固始汗时期驻扎在那里的和硕特蒙古部众,即文献记载中的达木八旗。不仅是蒙古族融入到藏族之中,也有一部分藏族为了生计或通过婚姻等方式融入到了蒙古族中,如最早分布在今曲什安河上游的叶龙沟、格科以及切雄河上游云龙沟、昨甘拉瓦(今花石峡)以南的阿柔部落,在和硕特蒙古占据青海后,阿柔成为其属民。后因与果洛部争夺牧场受挫,部分部众于乾隆末年、嘉庆初年途经格科(今果洛玛沁县境内)至多木科(今果洛玛沁县境内)一带,投靠黄河南蒙旗,成为前首旗部众,形成中部阿柔,又称藏阿柔。同时也有蒙古族与其他民族通婚融合的。虽然也有一部分青海蒙古族保留着其传统文化,但其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同周边包括藏族在内的其他民族融合。正如民国学者李自发所言:“青海境内汉、蒙、回、藏诸族,同居杂糅,历数千年,种族血统已混淆不清,今欲求纯粹血统之汉人或回人,事实上已不可能”。[32]第二,由于聚居区域的不同,青海蒙古的语言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早期由于受藏传佛教、蒙藏交错杂居的影响和青海蒙古上层的提倡,藏族语言文化被青海蒙古族所接受和使用,藏化是其社会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正如徐珂所说;“青海蒙、番杂居,番族所用之物,蒙族无不用之;番族所食之物,蒙族无不食用之,至番族所言,蒙族亦能言,而蒙族之服用、饮食、言语,则番族有不能兼之者。此则自然之习惯,不可强也”。[33]至于尚能保持自有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的蒙旗,也因佛教教义的熏陶,“都在被受西藏文化的激荡,改变自有文化的可能中”。[34]民国时期,驻牧在湟源、海晏、门源、共和等地的蒙古王公贵族也开始招募汉、回等民族,发展农业生产。大量的汉、回、土族群众为了生计,不断进入蒙地,这些地区的蒙古民众已渐趋汉化,以农业为主,游牧为副,居住比较偏远的蒙古族游牧为主,农业为副。[35]后随着与汉人交往的频繁,及现代教育的兴起,汉语在该区域得到了广泛流传;青海湖南岸、东岸的蒙古人则因通婚等原因,语言、服饰等方面逐渐藏化,后又汉化,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硕特南左末旗部分蒙古人用蒙、汉两种语言交流。[36]驻牧于柴达木地区的和硕特部西前旗、西后旗、北左末旗、北左旗、北右末旗、西右后旗、西左后旗、西右中旗等八旗蒙古人,前已述及,由于地理上相对封闭,自然环境恶劣,受环境限制,与盆地外蒙古人隔离,盆地内各蒙旗联系紧密,故该区域部分蒙古民众至今依旧操蒙古语,使青海蒙古族的语言文化得以传承。即便如此,柴达木地区蒙古族文化也受到藏族影响,在服饰等方面出现了藏化。[37]地处黄河以南的和前首旗、和南左中旗、和南右中旗、土南前旗四旗蒙古人,与黄河以北二十五旗蒙古在地域上隔绝,周边又被藏族部落所环绕,其蒙古王公上层率先接积极推广藏族的语言、文化、习俗,其“言语习惯生活皆藏化”。[38]但又保留着一些本民族文化的痕迹,成为处于蒙藏之间的一个特殊族群。[39]据调查统计,截止目前,青海蒙古人口约十万,其中五万人已经失去母语,分别使用汉语或藏语。使用藏语的人有三万多;另有两万人既使用母语,又掌握了藏语或汉语。通用的文字基本上以汉语为主,其中有两万人完全使用汉语、汉字。[40]
总之,清民国时期青海蒙古族社会语言文化总体上呈藏化趋势,因受地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加之同周边其他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的交流,呈出多样化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1]孙竹.蒙古语文集[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3.
[2]才仁巴力,青格力.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注释本、蒙文)[Z],北京:民族出版社,9.
[3][11][31]卓仓·才让编著.黄河南蒙古志[Z].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4]青海省志纂委会.青海历史纪要[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5][9][22](民国)周振鹤.青海[Z].北京:商务印书馆,:62.61.62.
[6][37]南文渊,可可淖尔蒙古走向边缘的历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7:-.-.
[7][俄]崔比科夫,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M],王献军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41.
[8](民国)李自发,青海之蒙藏问题及其补救方针[J].西北论衡,,[5](ll).
[10][23]清世宗实录,卷二0[Z],雍正二年五月戊展.
[12][13][18](清)仲优·昂青嘉布,先祖言教[M].香札·噶布藏确吉坚赞整理,多杰仁青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8:—..—.
[14]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县志·第七编·社会·方言[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5](民国)魏崇阳.西北巡化[J],新亚细亚,,[8](5).
[16]萧瑛,黄河南亲王和她的母亲[J].妇女月刊.,[4](4).
[17][38](民国)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M].胡大凌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3:..
[19](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M].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48.
[20]蒲文成.青海的蒙古族寺院叨.青海社会科学,,(6).
[21]张元彬.青海蒙藏两族的经济、政治及教育[J].新青海,,[l](10).
[24]铁穆尔主编.祁连蒙古志[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41.
[25][26]王云,青海藏族阿柔部落社会历史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81..
[27](民国)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Z].北京:中华书局,:.
[28](清)杨治平纂修,何平顺,周家庆,陈国壁标注.丹噶尔厅志·人类[A]//青海地方旧志五种[Ml.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9]王璐.加强对周边藏区乃至藏区周边的研究——从西藏、藏区、藏文化圈谈起[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
[30]靖唐.康北的重镇一甘孜[J].康导月刊,,[5](1).
[32](民国)李自发,青海之蒙藏问题及其补救之方计[J],新青海,,[1](12).
[33](民国)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Z],北京:中华书局.3:2—2.
[34]张元彬,青海蒙藏两族的经济、政治及教育[J],新青海,,[1](10).
[35](民国)顾执中,陆贻.到青海去[M].董炳月整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37][丹麦]亨宁·哈士伦,蒙古的人和神[M].徐孝祥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39]萨仁娜,自我与他者一河南蒙古族文化建构视野下的民簇认同差异[A]//西北民族论丛(第九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0]纳·才仁巴力编.德都蒙古民间文学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7—8.
注释①咱雅班第达,年—年,是和硕特部古鲁格沁鄂托克桑噶斯家族巴巴汗的第五个儿子。5年被卫拉特的盟主、和硕特的拜巴噶斯认为义子,奉献出当了陀音,从满珠习礼呼图克图受了沙弥戒。他为格鲁派在卫拉特的传播和蒙古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ND往期推荐
青藏高原多民族聚居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青海湖流域湿地保护中农牧民权益保障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共和县元者村的田野调查
青海古代民族弓箭文化考述——以羌、鲜卑、吐蕃为例
▼更多精彩推荐,请转载请注明:http://www.tdghe.com/wgkjbzd/82927.html